




河涌曾是护城河、商贸动脉,也是广府人的日常活动场所,河涌文化成为广府文化的一部分
人们称广州为“水城”,不仅因蜿蜒穿城的珠江,更因城内密布的河涌水道。自古以来,广州就是一座建在水上的城市,河道交错如巷陌,水系繁密形成水网。人们逐水而居,与水共生。如今街巷名中,仍可见“濠”“涌”等水脉印记。这些河涌曾是广州建城之基,先民生命之脉,载千年商贸繁华,育独特广府风情,刻下了城市扩张、商贸兴衰与文脉传承的年轮。

河涌水质清透,吸引白鹭嬉戏觅食。
河涌密布 水道交织
●古代广州城内有六脉渠,城东有东濠涌,城西有西濠涌,城中有南濠,城南有玉带濠,交织成网;城外更有驷马涌、荔枝湾涌、沙河涌等河涌密布如织,共同构成“六脉皆通海,青山半入城”的独特山水格局。
西北入城黄金水道 陆贾驷马涌登岸
宋代以前,在广州地域流淌的溪流,基本上都是天然形成的水道,少有人工开凿的河渠。西关平原地势呈向西倾斜之态,故天然水道都是向西流和向西南流。密布其间的主要有驷马涌、上西关涌、下西关涌、柳波涌、荔湾涌等几条大涌。在荔湾路与西华路交界处,有一条看上去平平无奇的河涌——驷马涌,便是其中一条。在古代这可是一条满载故事的河涌。
驷马涌发源于越秀山兰湖洼地,它曾是古代西北方向进入广州城的黄金航道。关于驷马涌的最早记载可以追溯至汉代。汉高祖十一年(公元前196年),汉大夫陆贾奉刘邦之命招安赵佗,他乘船经驷马涌登岸,在涌边筑泥城、植荔枝。陆贾此行不仅促成了赵佗归顺汉朝的历史大事,他亲手栽种的荔枝林让“荔枝湾”的美名流传两千余年。根据屈大均在《广东新语》里的记载,赵佗后来在广州城西的戙船澳(意为可以泊船的海湾)盖了一座越华楼赠给陆贾。
后世又称戙船澳古渡头为拾翠洲。从汉代到唐代,船只大都沿西江、北江而来,必经增埗河转入驷马涌,在拾翠洲上岸再进入广州。唐代诗人陆龟蒙在《奉和袭美送李明府之任南海》中所咏的“春尽之官直到秋,岭云深处凭泷楼。居人爱近沉珠浦,候吏多来拾翠洲”,正是当年码头官吏云集、船只穿梭的生动写照。相传河涌常现四匹马拉的官车迎送场景,“驷马涌”的名号便由此传开。

驷马涌两岸绿树成荫,环境优美。
南汉雅称“流花水” 明代赵介坠涌成趣闻
古时的驷马涌水深且水面宽阔。这一带风景优美,南汉时在涌上建起彩虹桥,彩虹桥横跨在水面宽阔的驷马涌之上,被宋代的人称为“长桥”,一个“长”字足以体现驷马涌当年水面之开阔。
这条河涌还流淌着浪漫的气息。相传南汉皇帝在芝兰湖边修建芳春园,宫女们晨起梳妆时抛入河中的残花,让河道有了“流花水”的雅称,由此更衍生出流花桥、流花湖的浪漫地名。相传宋代时孔子的一支后裔从韶关南迁,来到驷马涌边见到迷人的景色,便不愿再走,在此建起楼房园圃,安居于此。
元末明初,人称“南园五子”之一的诗人赵介来到驷马涌畔,欣赏小桥流水着了迷,凭栏远眺时失足坠涌,事后他不仅不懊恼,还赋诗“自谓谙水性”,留下南园诗社的一段趣闻。
清朝时期,靖南王耿精忠麾下将士经常在驷马涌给军马饮水、洗澡,故此地又称洗马涌。后来,人们觉得“洗马涌”这个名字不好听,曾改为音近的“司马涌”。直到清代以及民国时期,驷马涌仍是进城的重要水道,也是每年端午赛龙舟的场所。
随着历史变迁和地理发展,河道渐渐变窄,驷马涌曾经的传奇已经淹没在了历史尘埃之中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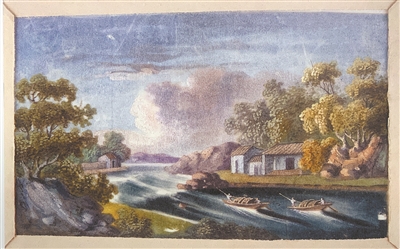
水乡风光图(清代广州外销通草水彩画)
凿濠通舟 商贸繁华
●宋代,广州相继修筑中、东、西三城,史称 “宋三城”。筑城同时,水利工程大规模同步展开:开凿南濠作为内港码头,为商船避风并便利外贸,凿玉带濠为城南护城壕;城内则利用天然河道与干谷开凿“六脉渠”,引渠水汇于城濠,再注入珠江。城濠与水渠相互贯通,逐渐形成“河涌通濠、濠通江海”的水运网络,兼具运输、商贸、防火与排涝功能。
千年濠涌缔造“水通财通”商业传奇
南濠 商船云集避风港
今海珠中路原名西濠街,东侧却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南濠街。南濠顾名思义在城南,不过,为什么南濠却在宋代的城西呢?《广东通志》记载:“南濠在城楼下,限以闸门,与潮上下,古西澳也。”原来当时人们将南濠称为“西澳”。
最初的濠除了是护城河,还有一个重要作用,是给商船做避风港。唐宋时期,中外商船多泊于西澳码头。珠江北岸直抵大德路南侧,江面宽逾千米,商船常遭风浪。宋景德年间,广东经略使高绅主持修筑南北向的濠涌,濠口建挡潮巨闸,使西澳成为广州最大的内港码头。
高绅还在附近建起了有“南州冠冕”美称的共乐楼,这是当时广州的最高建筑物,登楼极目远眺,可观羊城之壮美。广州知州程师孟挥笔写下《登共乐亭》诗:“千门日照珍珠市,万瓦烟生碧玉城。山海是为中国藏,梯航尤见外夷情。”此地一带的繁华可见一斑。
明代后,由于珠江北岸向南推移,加上泥沙淤塞,西澳逐渐丧失码头功能。加上重修西城墙,城墙从海珠北路、海珠中路移至今人民路,有了新的西濠,人们才渐渐把这里称为南濠。
玉带濠 朱楼画榭胜秦淮
在修筑古西澳的同时,广州着手开凿城南的城濠。这条城濠旧称“南濠”,后来经过多次疏浚与拓展,最终修成了东连东濠、西接西濠的宽阔城濠,蜿蜒绕城。因其像玉带那样围绕广州城南,故于清代得名“玉带濠”。
玉带濠的开凿,极大地促进了两岸商业的蓬勃发展。几座小桥横跨在玉带濠之上,其中,归德桥畔的濠畔街最为繁华。屈大均在《广东新语》中这样描绘:“濠畔街当盛平时,香珠犀象如山,花鸟如海,番夷辐辏,日费数千万金,饮食之盛,歌舞之多,过于秦淮数倍。”由此可知明代广州濠畔街之盛。
玉带濠两侧的高第街、濠畔街因航运便利成为商贸中心。濠畔街在明清时期,更是凭借众多的乐器作坊和精湛的乐器制作工艺,成为驰名中外的“乐器一条街”。明代时,水运将硬木运至濠畔街,渐渐地,这里出现了许多酸枝木器作坊,到了清代,数量多达数十家,濠畔街因此被称为“酸枝街”。
最引人注目的,当数玉带濠两岸林立的票号与会馆。当时的广州,各大商帮云集于濠畔街一带,其中晋商实力最为雄厚,他们开设的票号鳞次栉比。各大票号的建筑皆雕梁画栋,尽显富丽堂皇。
然而,到了晚清年间,随着近代银行业的逐渐崛起,玉带濠沿岸的票号会馆走向衰落。与此同时,濠畔街上涌现出不少从事皮革加工的作坊,这些作坊将废料垃圾随意丢弃到玉带濠中,导致河道污染日益严重。
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,玉带濠被改建为钢筋混凝土箱式暗渠。至此,这条蜿蜒流淌了千年之久的玉带濠,从此被埋入地下。
东濠涌 沿岸留下名人风雅
在广州老城区的众多古老濠涌中,只有东濠涌一直流淌到今天。
明洪武年间,永嘉侯朱亮祖将“三城合一”,文溪改道入城。成化年间,总督韩雍开凿黄华塘峡谷,引文溪水入东濠,形成全长五公里的水道,成为广州东城护城河与主要供水渠。
为什么要叫“东濠涌”呢?因为濠和涌是不同的,濠是护城河,涌只是一般的小河汊。东濠涌只有一段是护城河可以称濠,其他段只能叫涌,整条东濠涌是由濠与涌构成,所以叫东濠涌。
东濠涌的功能远不止于护城。从东江、北江驶来的商船多在东濠口泊岸,沿岸糙米栏、牛栏、猪栏密布,是四乡薪、米、木、竹等农副产品的集散地。直至20世纪70年代,东濠涌两岸仍为河滩,堆满粤北、粤东运来的木排,扛木工人的号子声曾经响彻老城的清晨。
不少名人亦在东濠畔留下了足迹。南宋探花李昴英在文溪筑桥;一代大儒湛若水建“湛家园”;“粤东三子”之一张维屏在清水濠成长;豪贤路有牡丹状元黎遂球;晚明名流陈子履兄弟筑“东皋草堂”结社雅集;岭南大才子鲍俊在芳草街建“榕堂”;水师提督李准建东园,鲁迅著书白云楼……东濠沿岸,流传着无数风流儒雅的故事。
2010年,经过生态治理后,东濠涌成为市民的亲水绿道。

东濠涌沿线已成为人们休闲散步的好去处。
西濠 造就城西繁华
明清时期,有一条水道与东濠涌齐名,对广州商业影响更为深远——它就是西濠。西濠原来是一条天然的溪流,在北宋修筑广州西城时修浚为城濠。明成化八年(1472年),督御史韩雍在上九路南侧开凿大观河,将位于西濠东侧的玉带濠引入西濠西侧的大观河,构建全城运河网,十八甫商业街因此兴起,成为西关最早的临水商埠。
明末清初,西濠两岸是个繁华鼎盛的商业区。西岸店铺参茸庄、银号绸缎庄密密麻麻,而在西濠东岸,绣坊、绣庄、戏服店、扇坊、金银首饰店,一家挨着一家。
西濠口外珠江河面上,聚居着成千上万的疍家艇。西濠口更发展为全城交通枢纽和商业中心——清末民初的港澳轮船码头、广三/广九铁路车站、粤海关、大新公司(今南方大厦)等机构均会聚于此,各大行栏也都聚集在西濠口一带。
“西濠的多次修浚,决定性地推动了明清两代广州城西商业发展,深刻影响了长达500年的城市经济脉络。”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副所长麦思杰教授如此评价。即便民国时期西濠被封盖为马路,西关的商业格局也早已定型。
如今,这些历史悠久的濠涌多数都已化作城市中的街道,但是水脉早已融入城市血脉,那些以“濠”命名的街道,仍在诉说着先民“凿濠通舟”的治水智慧以及“水通财通”的千年商业传奇。
水乡文化 人文摇篮
●河涌曾是广州城的“生命脐带”——既是防御外敌的护城河、贯通内外的黄金航道,更是催生市井繁华的商贸动脉,还是广府人的日常活动场所,其孕育的河涌文化独具一格,并成为广府文化的一部分。
依水而居孕育河涌文化
瑶溪胜景“河南”闻名
海珠岛分布着70多条河涌,但只有一条以“海珠”命名,那就是贯穿珠江前后航道的海珠涌。海珠涌由鸭墩涌、小港涌、马涌、三丫涌等组成,东起鸭墩水,西至凤凰岗口,全长5.83公里。以前人们常说“旧日河南,中通一滘”,指的就是海珠涌。由于这条水道的分割,令河南有“双洲”之称。1986年,经过整治后,这几段河涌被统称为海珠涌。
广州人更熟悉海珠涌的另一个名字——马涌。马涌的东段旧称瑶溪。据《海珠区志》记载:“瑶溪以二十四景闻名,成为旅游胜地。在其起讫两端,建有两座石桥,东端的名利济桥,西端的名汇津桥,是瑶溪二十四景的首尾二景。”
关于“瑶溪二十四景”之名的来由,不得不提到一个人。清道光年间,在瑶溪边长大的刘彤总结出瑶溪的二十四景,每景附一诗,遂成《瑶溪二十四景诗》。辗转多年后,居巢觅得刘彤的二十四景诗,将自己及友人写的诗歌编入,于光绪三年(1877年)出版。后来,不少书画名家以瑶溪为题材赋诗作画,瑶溪成为“河南”最出名的人文及自然景观。
“每次来到富力海珠城,我都会上利济桥走走。”市民胡女士说。这座横跨马涌的三孔梁式石桥,即是瑶溪二十四景中完整保存的一景——待月桥。刘彤有诗云:“待月月东升,溪光浩无极。烟村人静时,万物雪霜色。”后来木桥改建为花岗岩石,改名利济桥,有赐予恩泽之意。
历经百年变迁,瑶溪二十四景遗迹还保存有“石马岗”“待月桥”“合流津”等几处,与相邻的十香园、思复亭、晓港公园一同构成自然与人文交融的画卷。
马涌支流漱珠涌形似一条“小龙”,通向堑口与珠江相连,涌口的鳌洲小岛,仿佛龙口中吐出的一颗明珠,故有漱珠涌之名。清代,涌口与十三行商馆区隔江相望,是十三行行商建宅之处,也成为“河南”(海珠区)最早开发的地区。它还有一个别号叫“运粮河”。一艘艘木船将“河南三十三村”生产的粮食、瓜果、蔬菜运往城内,又从城内换回日用杂货,是连接城乡的重要商脉。清代初期的漱珠涌,夹岸遍植水松、垂柳,毗邻广州四大古刹之一海幢寺,再往远走一点就是以素馨花田闻名的庄头村,一派清丽的田园风光。20世纪六七十年代,漱珠涌被改造成为地下排污渠,从此在广州地图上消失了。
广府文化的“活态博物馆”
河涌串起的不仅是地理脉络,更是血缘网络。在水网密布的珠三角,纵横交错的河涌把村落串联起来。青年男女跨涌联姻形成“老表村”,同宗族群以“五百年前是一家”结为“兄弟村”。每年端午节前后,广州各村之间都会划龙船沿着河涌一村接着一村地巡游,拜候、探望邻村的亲戚、朋友。龙舟文化是河涌文明最鲜活的注脚,“龙船招景”更将河涌里演绎的激情推向高潮。
今年端午节的上午,锣鼓喧天、鞭炮齐鸣,一场热闹的“龙船招景”仪式在猎德涌上演,140个兄弟村社的150多条龙船会聚猎德涌。河涌一度舟楫相连,出现“堵船”的盛况。而在河涌两岸,挤满了围观的市民游客,欢呼声此起彼伏,场面十分热闹。“老表快靠岸”“上岸饮啖茶,食个饼啦!”见到龙船来,乡亲们的声声呼唤洋溢着热情。水中龙首轻点,船身三进三退——这是岭南龙船独有的“涌上叩门”古礼,每一次进退都是对主人家最郑重的问候。

每年端午节,猎德涌龙舟竞发,鞭炮声、鼓声、欢呼声交织成一片。
“我们7点多就从琶洲划龙船过来‘走亲戚’啦,吃块龙船饼,看看老表,图的就是这份情义,这份好意头。”来自琶洲的桡手郑先生说。猎德端午龙舟竞渡享誉海内外,每年端午很多外村龙舟来猎德“以舟会友”,一涌两岸人山人海,正是这年复一年的“睇龙船”“食龙船饭”“扒龙船”,蕴藏着村民们对彼此、对乡土深深的眷恋,诉说着河涌作为广府文化“活态博物馆”的独特价值。
地名俗语皆含河涌文化
西关大屋“三间两廊”多沿涌而建,后窗常设“水埠头”,昔日居民可从石阶直抵河面浣衣、汲水。曾经泮塘一带的骑楼,商铺面街,后院水埠头直接通涌,形成“前铺后水”的独特格局。荔枝湾的水上人家“疍家人”撑着小艇,艇上插一面写着“粥”字的黄旗沿江叫卖——这便是广州最出名的粥品之一“艇仔粥”的来源。
“月光光,照地堂,虾仔你乖乖瞓落床,听朝阿妈要捕鱼虾啰!”童谣《月光光,照地堂》陪伴了一代又一代广州人成长。对老广而言,河涌曾是童年的天然游乐场——钓蟛蜞、捉鱼摸虾、在涌边榕树下戏水……而地名里的“通津”(如寺贝通津)、“涌”、“濠”、“畔”(如濠畔街),以及方言中“水过鸭背”“水静鹅飞”等俗语,皆与河涌文化息息相关。
全民参与 河涌新生
●“河涌变美了,我的活也变轻松了。”谢全是驷马涌河涌保洁环卫工人,这位日均巡逻20公里的“河涌卫士”如是说。
生态治理 河涌变美
近年来,广州市投入了大量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,实施了一系列河涌综合整治工程。从截污纳管到清淤疏浚,从生态补水到景观提升,全方位推进河涌治理工作。
河涌治理离不开全民的参与。广州通过开展“畅享绿美广州 共筑清水梦”等各种宣传活动,鼓励市民参与到河涌保护中来。许多志愿者组织自发成立,定期在河涌两岸开展垃圾清理、水质监测等活动。全民参与的理念,让河涌治理成为一场共建共享的生态行动,凝聚起了保护河涌的强大合力。
每天清晨5点,天还未亮,驷马涌上传来的桨声已划破黎明的宁静。“谢师傅划船的桨声比闹钟还准时,风雨无阻。”在岸边晨练的居民说。
这位谢师傅就是驷马涌河涌保洁环卫工人谢全,这位日均巡逻20公里的“河涌卫士”,近两年清理了约20吨垃圾,推动驷马涌向水清岸绿转变。如今,驷马涌边建起了亲水步道,岸边孩童嬉戏玩耍,欢声笑语不断。今年1月,一张“河涌美容师”朝拾落英、守护花城的照片在网络流传。有网友留言表示:“这是城市写给春天的情书。”这张照片的主角正是谢全,当时他在岸边将紫荆花瓣和落叶摆成一颗巨大的爱心。“河涌变美了,我的活也变轻松了。”谢全说。
自然人文 和谐共生
在治理河涌的过程中,广州注重生态修复与人文保护相结合。在河涌两岸种植水生植物,打造生态湿地,为水生生物提供栖息地,恢复河涌的生态系统。同时,对河涌两岸的古建筑、古村落进行保护和修缮,将岭南水乡文化融入河涌景观建设中。
荔枝湾涌的改造便是一个成功的范例。2010年,荔枝湾涌揭盖复涌整治,村民积极建言献策。“拓宽河道弯位弧度,加宽整体河道,提升横跨河道的桥梁桥洞高度,避免船工发生碰头等事故……”至今,泮塘村村民李凯帆仍对具体提出的建议记忆犹新。
通过控源截污、清污分流等整治手段,融入文化游船、滨水戏台、水上花市等岭南文化元素,荔枝湾涌重现了“一湾溪水绿,两岸荔枝红”的美景。李凯帆说:“复绿的荔枝湾涌连着荔湾湖内的涌段,龙船水路超1.5公里,让西关龙船文化得以延续。”泮塘村的龙船“朋友圈”逐渐扩大,龙船文化氛围越来越浓厚。修复后的文塔、龙津桥等古建筑与河涌景观相得益彰,沿岸还开设了民俗博物馆、特色小吃店等,成为展示岭南文化的重要窗口。
如今的广州河涌,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。清澈的河水、摇曳的水草、嬉戏的鱼虾,再次成为河涌的常见景象。不少河涌两岸绿树成荫,休闲步道蜿蜒伸展,周末,许多市民全家出动,大人骑车带孩子赏景,年轻人戴头盔穿运动装畅快骑行……
河涌如弦,弹唱千年粤韵。
大小河涌入珠江
据《广州市·地理环境志》(1991—2000),汇入珠江广州河道的河涌纵横交错,市区共有大小河涌231条,总长度约913公里,分别汇入流溪河、白坭河及珠江广州河段,主要分布在黄埔区、天河区、白云区、芳村区和海珠区。
较大的河涌有乌涌、南岗涌、沙河涌、车陂涌、深涌、石井河、新市涌、黄埔涌、海珠涌、石榴岗河、花地河等。
“涌”为何读chōng
外地人初到广州,听到本地人将“河涌” 的“涌”念作“chōng”时,往往会感到惊讶。
“涌”字在古汉语中就有表示河汊、水流汇聚之意,且读音可能更接近如今粤语中“chōng”的发音。随着历史发展,普通话在语音演变过程中,“涌”字读音逐渐规范为“yǒng”,用于表示水向上冒、像水涌出等意思,如“涌泉”“涌现”;而在河网密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,河涌对于当地人的生产生活至关重要,粤语保留了“涌”字古老的发音和含义,成为人们对身边河流水道的特定称呼,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。
这种读音不仅是对地理环境的语言反映,更承载着广州人的生活记忆和文化认同。
 关注 · 广州政府网
关注 · 广州政府网